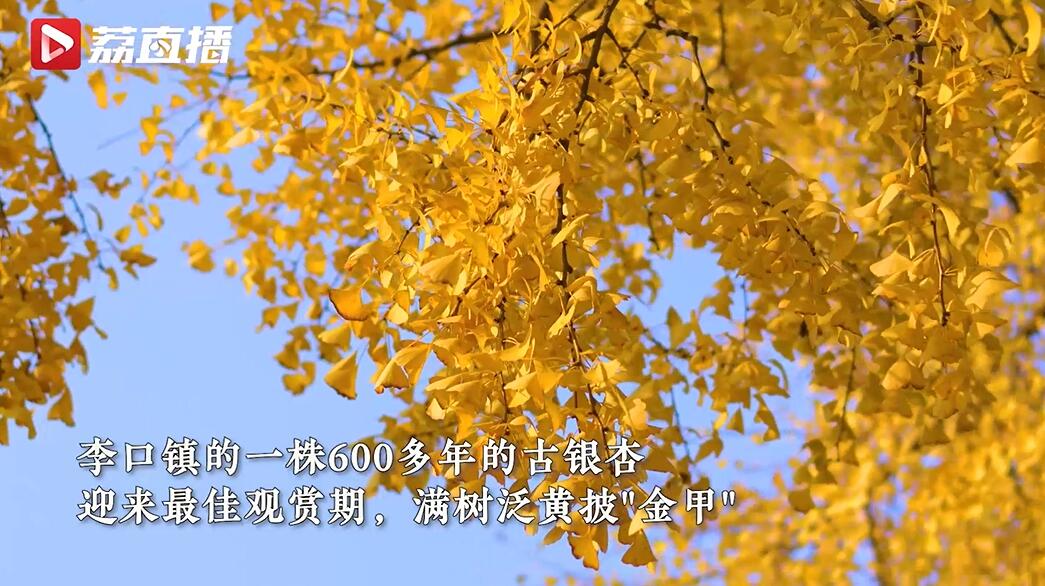《夜泊秦淮》之后25年,著名作家叶兆言最新长篇小说《刻骨铭心》由上海九久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策划出版。
这是一部以男人们为主角的群像小说、正气之作,书写男人家国情怀,兄弟情谊,描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风云变幻,裂变时代的痛与爱。比《夜泊秦淮》更大气阳刚、正气磅礴,堪称叶兆言新历史小说扛鼎之作。
今天(4月15日)下午2点,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将在南京凤凰云书坊24小时书店为《刻骨铭心》举行新书首发式暨读者见面会,叶兆言先生将亲临现场,解读新书创作,并与作家鲁敏展开精彩对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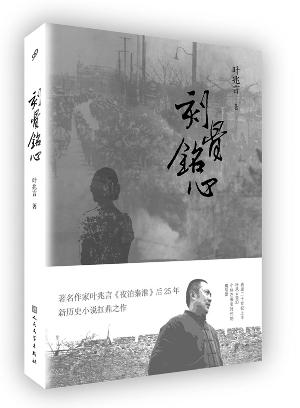
散文写多了,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写小说上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死水》开始,叶兆言从事文学创作已有数十年。
在当代作家中,叶兆言算是比较难被归类的一个,他由新历史小说成名,写过相当数量的新写实小说而进入文学史,又常常被置放在先锋文学的大范畴来论述和计较。
这些年,叶兆言的散文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用他在长篇小说《刻骨铭心》里的话说就是:“有评论家已把我归类到了散文作家的行列。有一家出版社正计划出版我的散文全编,粗粗计算了一下,竟然可以有二十本!出版社吓了一跳,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不过,他对于自己“散文家”的“副业”似乎也非百分之百认同,在一篇文章里,他有些自我反省地写道:“(散文)写得太多,搁在篮子里就是菜,给人印象不马虎也马虎了,想不潦草都不行。”
于是,最近几年,在结集散文的同时,叶兆言还选择了“重回起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重写新历史小说上,在《一号命令》《驰向黑夜的女人》等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中长篇之后,叶兆言又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刻骨铭心》。
小说走进“黄金十年”及“八年抗战”时期的民国旧都——南京的历史断层,让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虚化后退,请虚构的人物站上舞台中心,通过对一系列历史碎片的打捞与拼贴,将焦点集中在个体生命在大时代波浪翻滚下的命运起伏和生存处境。作者以平静的笔触,独特的视角,让历史与当下并行互文,勾画了一幅个体生命与混乱时代相互交融、激荡飘摇的风俗世情画卷。
重回新历史小说的维度
虽仍旧落笔历史,但又绝非单纯地写历史,甚至可以堪称一部“新新历史小说”。
整部小说共七个章节和一个后记,第一章里,叶兆言讲述了两则关联度不算太大的故事,一则是讲受高官同学之托,陪同一位董事长和年轻女郎游玩南京;另一则讲了因公去哈萨克斯坦采风的前后波折以及和一名当地作家的交谈。在这两则故事里,叶兆言塑造了一个身份、背景、经历都和他本人几乎百分之百雷同的“我”的形象,这个“我”竟然也正在写一部叫做《刻骨铭心》的长篇小说。虚构的“我”跳出了纸面,和真实的“叶兆言”不谋而合。
到了小说的中间六章,他“毫无征兆”地甩开了那两个似乎还没讲完的当代故事,另起炉灶重述1949年之前的时期,把绍彭、希俨、秀兰、丽君等一群小说人物,置放在了军阀混战、北伐、南京大屠杀、汪精卫叛变等历史事件之中,让他们活跃在桃叶渡、高云岭45号、瞻园路126号这些南京版图上的真实位置,并且促成他们和章太炎、魏特琳等著名历史人物发生了面对面的关系。周围的人地事都是真实的,唯有主人公是虚构的。
甚至他还在后记里用一本正经的语气介绍起2002年所写的《没有玻璃的花房》里的虚构人物李道始和这本2017年写成的《刻骨铭心》里的虚构人物俞鸿竟然还是下属和领导的关系。
或许叶兆言更想表达的还是——这些虚构人物的性格和情愫也都是真实的,只不过经过了组合和拼接,并被冠以一个难以辨识的人物名字。这就像叶兆言说过的那样:“小说不是历史,然而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
写作是我的“刻骨铭心”
关于这部小说,叶兆言说:“是一部群像小说,都是些小人物;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虽然是小事,对当事人来说,却都是刻骨铭心的事。”
比如书中描写了一个哈萨克族的中国作家,他用哈萨克语写作,还得了文学奖。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之后,他移民去了那里。他原以为,自己和族人在一起会如鱼得水,却没想到,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语和他用的哈萨克语很不相同。他失去了自己的文字,从此不能写作,在族人中成为了“异乡人”。
这是小说虚构的人物,当然有一定的生活原型。叶兆言借用了他的经历来描述文字对于写作者的刻骨铭心。
“中国这么大的疆域,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统一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了同一种文字——汉字。如果汉字拼音化,统一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各地发音不一样,沟通都很困难。这就是文字的力量,我们应该感谢汉字。”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文学人物身上有着叶兆言自己的影子。对此他回应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写作确实是我的‘刻骨铭心’。我每天一早起来,电脑一开,就开始写,每天写六小时以上。有时候写得疯狂了,家人、孩子也都不怎么理解。从某种角度看,这样的生活比我年轻时骑行200多公里更加疯狂,因为这是我给自己判的无期徒刑:没有目的地,会一直写下去。”
叶兆言现在用电脑写作,看似轻巧,其实每天也就写千把字。当然也有高峰状态下日产数千言的情况,但千把字是常态。
他说,写作的人生,就是不断地和写不下去作斗争,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来源:现代快报 编辑/马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