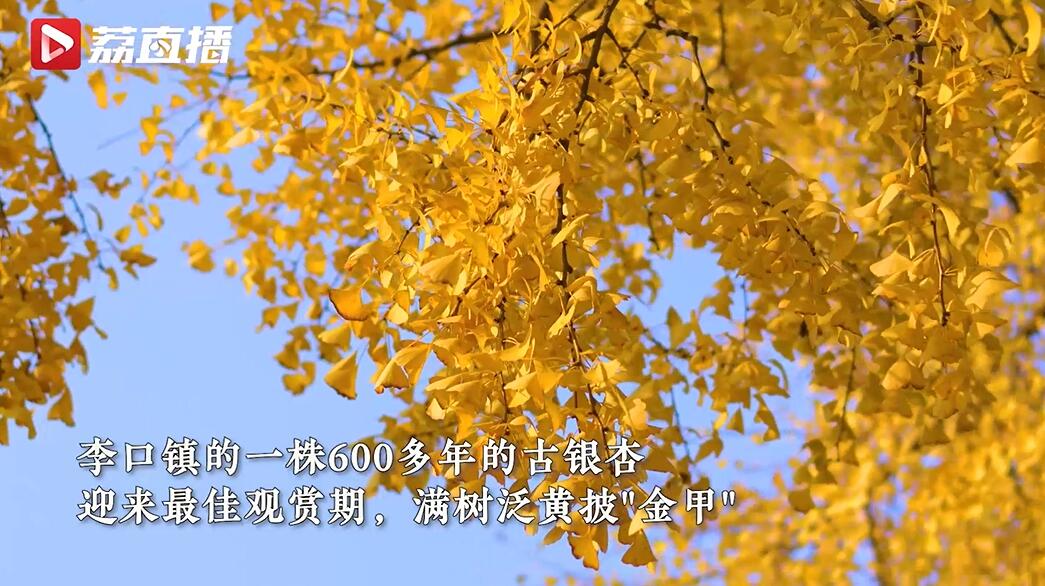虽然现在任教于悉尼大学,来南京的机会不多,但石俊山却习惯地说是“回南京”,因为他曾在这里生活工作多年
出生于1981年的加拿大小伙石俊山,说中文的流利程度令人称叹,语速比中国人还快。
从16岁开始学习中文,他便和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南京,他曾任南师大外教、在南大读博、就职于江苏省昆剧院,这每一个身份都和南京这座文学之城融为一体。“我住在南京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生活在南京的一个人,我最靠近的就是在南京的那些文化。”难能可贵的是,这份融入即使在他今天已经定居悉尼了也未曾改变。
石俊山是在加拿大温哥华长大的,1998年他高二时有了一个机会到香港读书。学校鼓励他们学普通话,他的中文基础就是那时候打下的。
两年后,他并不着急考大学,只身一人作为交换生来到北京,在牛栏山一中教了一年英文。学生的年龄与他相仿,石俊山很快与他们打成一片。
中文的学习对石俊山来说,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他说,小时候在加拿大,身边的华人就很多,他从来不会觉得这些有什么神奇,所以一直以来,他都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探寻者,而是身处其中自然而然融入了中国的文化。
结束牛栏山的教学,石俊山去了美国念哈佛大学。他选择了东亚语言与文明这个专业,继续修中文课。他的理由听上去特别简单:“如果不修中文课,我中文一会儿就会没了,一会就会全部忘记了。”
跟其他的同学相比,因为石俊山中文学得早,所以开始读本科的时候语言早已不是问题,能看书能交流,所以他可以直接上一些有文化内容的课。比如,他上了一些戏剧的、文学的课,选了孔子孟子儒家的课程,也会学元杂剧什么的,还会学20世纪的中国文学等,以中国文化为主。
其间,石俊山申请了哈佛的燕京奖学金,所以2004年有机会到了南京大学念书。
那时候,石俊山对南京并不了解,只知道它是民国的首都,知道一些六朝的往事,他到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哪里可以看戏。“我喜欢舞台,从小就看戏,在温哥华是看歌剧、话剧、音乐剧那些东西,到了南京,我就会找这里礼拜六的晚上到哪里才有戏看。”
就这样,他找到了昆曲。
2006年,昆曲《1699·桃花扇》在南京和北京亮相。
与中文唱词同时出现在屏幕上的英文版唱词简练优美又不失古典的韵味。在北京首场演出之后,时任《1699·桃花扇》文学顾问的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老先生赞叹不已:“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英文翻译!”
“秦淮烟月无新旧,脂香粉腻满东流”,“金粉未消亡,闻得六朝香”,这些文言的句子,翻成白话文尚且需要一定功力,更别说是翻译成英文了。而得到余老赞赏的英文翻译正是出自石俊山之手。
石俊山谈到与昆曲的相遇,分享了一件趣事。南大的课堂上,老师讲到了昆曲《牡丹亭》,于是石俊山就想去看看。他好奇地问同学:什么是昆曲?同学“误导”他,说是昆明的戏。石俊山满腹思索:昆明的戏怎么在南京演?于是在一个礼拜六的晚上,他和一个德国同学跑到位于朝天宫的省昆剧院,正好赶上了一场昆曲表演。
“那个时候说实话我是看不懂嘛,但是你看得出来,它背后有很多东西,你看得出来它深奥。”石俊山说。
昆曲,向石俊山打开了一扇门。他很快成为昆剧院的义工,帮忙翻译字幕,接待外宾或者外出演出,他也都随行,在中外交流方面贡献不少,很快成为了正式员工。
“能在昆剧院工作,接近了我喜欢的戏,能了解很多东西,天天看他们排练,工作环境特别的有韵味。”石俊山就这样迷上看昆曲。

随着他的深入了解,石俊山发现,西方也有人在研究昆曲,但是他们并不了解当代的舞台,他们可能研究《牡丹亭》《桃花扇》的文本,但是现在昆曲是这么演的他们未必了解,而这些剧院演员的日常生活,其实也是表演艺术的一部分。
石俊山认为,在昆剧院的学习,比他呆在西方埋头读书能了解昆曲和中国文化更多,特别是这种表演艺术在当下的中国怎么样生存、发展、传承这一类的问题,是他呆在剧院里才会了解的。2007年,石俊山回加拿大读硕士,但与昆曲的缘未了。导师是一位主要研究明清传奇跟明清小说的老师,写了关于《牡丹亭》的一本书,叫做《舞台上的牡丹亭》。
关于昆曲的研究还在继续。“有的东西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研究不完的,你可以花一辈子,你会得到很多东西。但是你不要追求来一天就全知道全懂,没有的事,昆曲的魅力就在于不太可能让你全部知道了,它是一个很浓厚的文化体系。”石俊山用一句听着有些绕人的句子,阐述了昆曲的魅力,似乎也阐述了中国哲学。
石俊山再次到南京是2010年。
此前一年,石俊山在上海世博会加拿大馆工作,他接到了南师大一个老师的电话:“有没有兴趣到南师大去教书?”这位老师也是因为看了石俊山当时在昆剧院翻译的字幕非常欣赏,才会做这样的引荐,石俊山就此成为南师大的外教。也是这个原因,使他又得到了在南京大学文学院读博士的机会,因为那会儿南大做戏剧方面的老师都知道昆剧院有一个外国人在做翻译。
石俊山说,他比较感兴趣的是中国元明清的文学,他会觉得自己很靠近他们,没有太大的隔离,这种感觉很朴实,而更早期的文学,他尽管知道典故,知道故事,却不会觉得很了解那些写作品的人。
他很喜欢这种和古人心心相惜的感觉。“我比较了解已经有戏曲剧本传到现在的,大概从元朝开始的那些人。我看一个明清的小说一个传奇,没觉得这些人的行为有什么奇特的,这些人的行为好像都很能理解,我可以赞成,可以不赞成,我可以很佩服,可以很讨厌,但是不会觉得这人是什么意思。”石俊山笑道,也许这是他的幻象,但他非常享受地沉浸在这种幻象之中。
所以,他也不会觉得元明清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有很大的断层,古代与现当代文学在他的心目中是契合的。所以他翻译昆曲,也会翻译现当代文学。因为来了南京,就想知道谁在写南京的故事,所以就会去看苏童、叶兆言、毕飞宇,发现有一些作品没有被翻译,他就会找来翻译。目前翻译出书的有苏童两本书、叶兆言一本,还有一个汇集不同作家的中国当代小说。
博士毕业后,石俊山又回到加拿大念博士后,从2017年起在悉尼大学任教,教中国现当代文学、古代戏剧、世界文学等课程。
现在来南京的机会不多,但石俊山却习惯地说是“回南京”:“你看我现在回南京我都是看已经认识十年的朋友,你的朋友是谁,你就对什么文化感兴趣。我从16岁到现在37岁,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中国,特别是我住在南京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生活在南京的一个人。”
对话
文学没有边境
读品:怎样才能把昆曲的英文翻译做好?
石俊山:我大量看诗,做一个好的翻译家不仅仅“信”要到,还要“达”,“雅”也必须有,雅不雅主要看你对英文的感觉,就要看谁对语言的感觉最细腻最正确最感人。如果我翻得比较好,大概是因为自己对英文诗歌的了解和感觉是比较深的,好像自夸了。还有一点,昆曲的戏什么典故都有,它本来就是一个文学作品,你如果翻《牡丹亭》,你不能不了解一些佛教的思想;你翻译《桃花扇》,你不能不了解明末清初的那段历史;你翻译《长生殿》,你不能不了解杨贵妃跟唐明皇的故事。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自然而然的,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无法翻,你翻了就会加深对这些东西的理解。
读品:您和余光中先生有过什么交往吗?
石俊山:余老师的英文、中文都非常的精通,而且专门写诗歌的,翻译诗歌的。我那个时候也不认识余老师,他在北京,专门请我喝茶聊一聊,然后跟我说他觉得我翻得不错,也提了一些想法,然后鼓励我继续翻译,继续写诗。
读品:中国文学研究很看重海外学者的声音,也想听一听您的看法。
石俊山:我没觉得外国人看中国文化应该从一个很远的距离去看的。我就觉得你把它当作文学,你把它当作戏剧就好,你就会感兴趣。当然前提是一个不错的作品。包括我教书,比如说我下个学期就要教一个20世纪戏剧那么一门课,就有易卜生、契诃夫,也有曹禺有老舍什么的,我不会说,现在我们念的、看的是一个中国的话剧或者事物,或者古代一点的,我觉得什么法国古典戏剧或者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跟汤显祖、孔尚任、关汉卿的作品一起看完,我是心里有那么一个文学世界。我自己没有觉得有那么大的距离,特别是现在我在南京,明天我就在悉尼,我在这里跟你讲中国文化,或者我在澳大利亚讲澳大利亚文学什么的,我不会觉得有很大的差别。
读品:您目前在读什么作品?
石俊山:我今年在看的是徐霞村的作品。我觉得他可能是不太被人知道的一个民国作家,然后他写得很有趣的,一会是北京一会是巴黎。那个时候民国出去的那些作家文人什么多的是,钱钟书写外国也写得很有趣,胡适什么的一直都是一种挺多元的视角。
中国人外国人都可能会觉得中国文学就是一个个体的、单一的东西,然后你把它从《诗经》念到莫言就把它念完了。文学史也是这样教的。但是我是觉得当代的中国或者说华文文学非常的丰富,也有很优秀的新加坡华文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等等。另外,平时我们看的很多都是大都市的那些小说和诗歌,但是你如果花一点时间去看福建在写什么小说,云南在写些什么诗歌,也是有很有意思的,港台的文学风格也会有它的特色。我觉得不要只看一个文学史。要把它想得丰富一点,多元一点,这才是文学,文学没有边境。
(来源:现代快报 编辑/钱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