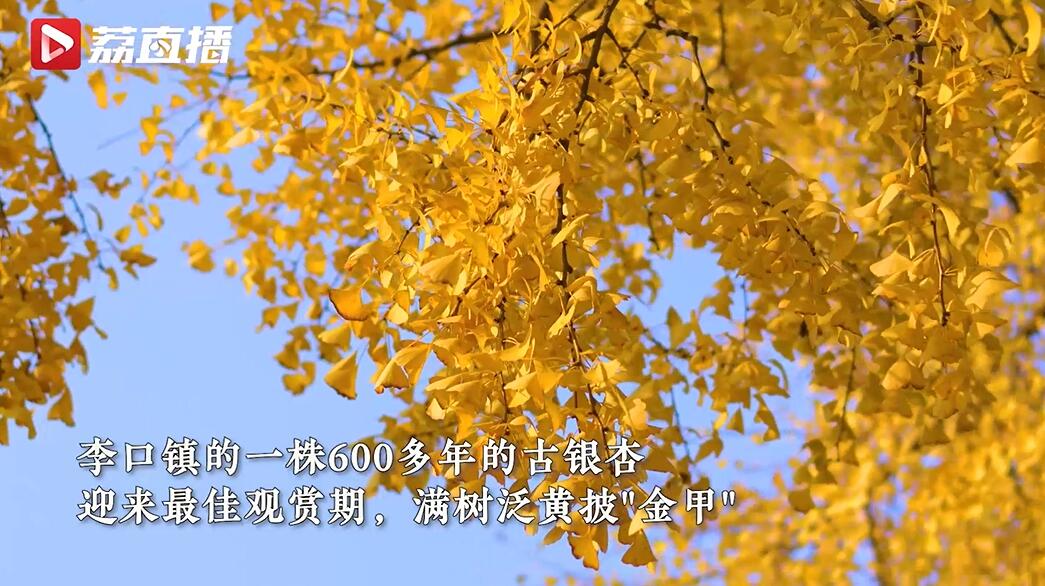2017年12月16日下午5时,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屠岸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4岁。
时间向前推一年,2016年3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65周年的茶话会上,93岁高龄的屠岸在演讲的结尾,用浑厚而不失儒雅的声音说道:“扬帆吧,人文人。‘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始终对中国出版的未来充满希望。
2016年8月,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在上海复兴中路的思南文学之家,屠岸以莎士比亚译者的身份,应邀前往上海。2016年10月,北京大学,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年会召开,屠岸出席。作为中国第一部中文全译单行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译者,屠岸重拾译笔,重译、修改、增补了旧时译文,原因只有一个:“这是我一辈子的工作。”
2017年1月,周有光先生去世。追思会上,屠岸用周先生生前非常喜欢的“常州吟颂调”吟唱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中气十足。
直到去年,屠岸先生依然保持每天六七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伏案阅读、写作、记日记、给读者回信。他曾开玩笑说,如果上帝再给他十年时间,他的诗歌创作生命将更加充实。

诗才初露
“只要是诗的殿堂,
我就是向那里进香的朝圣者”
1923年11月,屠岸(原名蒋壁厚)生于江苏常州文笔塔下的一个书香门第。文笔古塔,在常州人心目中是“笔魂”的化身,冥冥之中,屠岸的一生与笔墨诗画勾连在了一起。母亲屠时是当时常州了不起的才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不所不通,尤擅诗词丹青。屠岸儿时的家中,挂着这样一副对联:“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家中浓郁的文化氛围浸润着幼年屠岸,小学三年级时,母亲便教他读《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唐诗三百首》《唐诗评注读本》。“从那时起我成为诗歌的朝圣者,一生不辍。”回忆起那段时光,屠岸记得,母亲会先解释诗文,再以“常州吟诵”的方式,带领屠岸,像唱山歌一样一句句吟唱出来,虽然不一定完全理解,却别有一番兴味。此后的几十年里,屠岸都喜欢在入睡前吟诵诗歌,从李白、杜甫、白居易,到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济慈。他曾和朋友打趣,“每天我不用服安眠药,我服的是‘诗药’”。

《济慈诗选》
作者:济慈
译者:屠岸
版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年11月
1936年,13岁的屠岸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他作别故乡常州,借宿在上海姨母家中。“天上是孤独的月亮/我站在操场上/想那些衣不遮体的穷人……北风呼呼,如狼似虎;星月惨淡,野有饿殍。”一个冬夜,少年屠岸难以入眠,便起身吟起了这首《北风》,灵感来源于姨母家门口冻死的乞丐。略显稚嫩的诗行,开启了屠岸诗人的征途。五年后,他在《中美日报》副刊《集纳》上发表了第一首诗《孩子的死》。读高中时,屠岸开始学英文诗,受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表兄奚祖权影响,他陆续阅读了《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作品选读》等书。他把100余首英诗的题目抄在纸上,粘在墙上,用飞镖投掷过去,扎到哪一首,就找来那首诗研读。两年时间里,他读遍了百余首诗,慢慢爱上了英诗,特别钟情于济慈、惠特曼,痴迷于莎士比亚。屠岸自己彼时或许并未预料到,1950年,他执笔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一生与莎士比亚“结下”不解之缘。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
作者:威廉·莎士比亚
译者:屠岸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3月
“尤里卡”的幸与命
“我喜欢济慈的诗,因为他用美来对抗恶”
屠岸爱诗。相传有一日,他正在理发馆理发,心中默诵英文诗,突然领悟到济慈的一句诗的意义,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呼“好诗”。理发的师傅惊得目瞪口呆。两千年前,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顿悟到计算浮力的方法,从浴缸里站起来,喊出一句“尤里卡”(古希腊语,意为“我找到了!”)。于是屠岸获得了“尤里卡”这个绰号。1943年夏天,屠岸到江苏吕城农村过暑假,在鸟鸣啁啾的乡野之上,在夜晚被灯光染黄的麻布帐里,他通宵达旦地写诗,修改,默诵,誊抄,50余首诗喷薄而出,屠岸第一次进入诗歌创作的高潮。入夜,他高声朗诵自己的一首诗“天地坛起火了”,声音惊动了隔壁的沈大哥,后者误以为着火了,从房间里奔出来,得知原委后称屠岸为“诗呆子”。

屠岸手稿
因为爱诗,所以才会把一生都给诗。正如屠岸自己所说:“我是诗的恋者,无论是古典,浪漫,象征,意象;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只要是诗的殿堂,我就是向那里进香的朝圣者。”在对诗澎湃的热情的推动下,1948年,屠岸翻译出版了惠特曼诗选集《鼓声》。1950年,由屠岸翻译出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成为第一部中文全译单行本。67年来,屠岸亲自执译笔,历经500余次修改,后不断再版,累计印数达60多万册,历尽磨砺,终成经典。
“文革”期间,尤里卡、诗呆子屠岸双手挥舞着镰刀割高粱时,心中默诵的,依然是他最爱的济慈、惠特曼。他一步一割,心中诗句的节奏跟着步伐抑扬顿挫,停停行行。“My heart aches, 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 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书被收走了,但心中镌刻的诗句不会褪色和离开,济慈的《夜莺颂》回荡在属于屠岸的田野,陪他渡过一个又一个难以入眠的夜。2001年,屠岸历时三年翻译的《济慈诗选》(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翻译奖。他说:“我为什么喜欢济慈的诗,因为他用美来对抗恶。”从少年时代开启的这段缘分,就这样缓慢而持久地延续着——墙上手抄的诗歌,羽毛飞镖,山野与高粱,鲁迅文学奖……在深谙翻译之道的屠岸看来,“真正要译好一首诗,只有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灵魂的拥抱,两者的合一”。翻译时笔尖与纸页碰触的刹那,屠岸就是济慈,是惠特曼,是莎士比亚。

《屠岸诗文集》
作者:屠岸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没有新鲜感就没有诗,我每天看到东西都是新鲜的,太阳存在亿万年,但是每天看它都是新的。我完全可以做一个婴儿,去拥抱生活。把每一天看作新的生命的开始,就不会萎顿、不会沉沦。”尽管痛过,伤过,恨过,也感动过,追求过,痴迷过,屠岸却始终都像一个婴儿那样,张开手臂,和善微笑,拥抱生活与世界,迎接痛苦和生命。
他说过:“女儿问我来世希望做什么,我说,还是做诗人。我不会当小说家,爱画画,但也不一定当得成画家;如果是当动物,最好变成一只小鸟。”
一路走好,诗人屠岸,愿你成为一只随时可以起飞的鸟。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