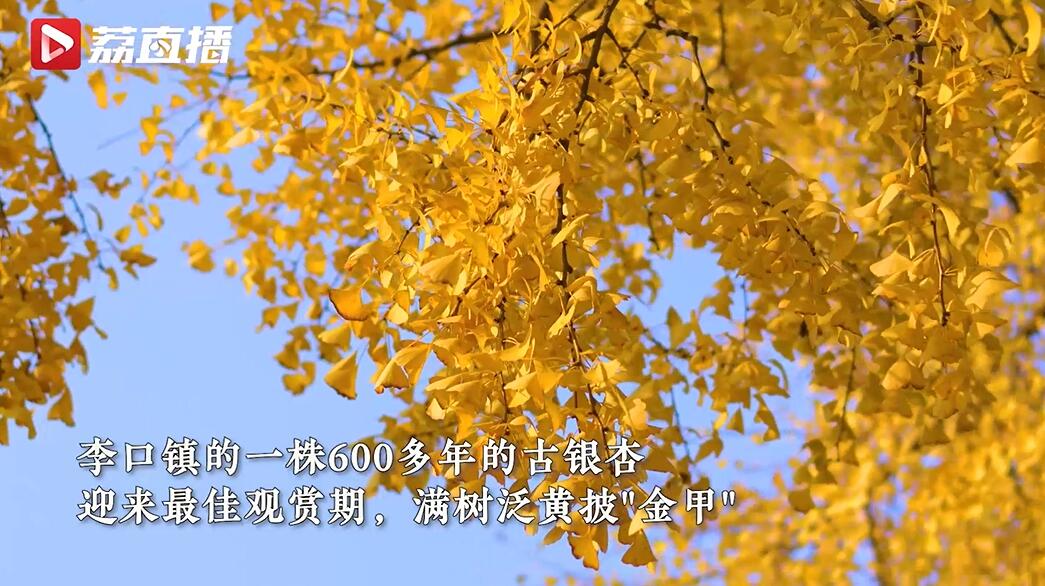在我的家庭档案中,保存有两张社员证,一张是父亲的,一张是母亲的。闲来无事,翻阅两证,一股思绪便不由自主地飘飞到那挣工分的岁月。

交公粮(图片来自网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管理体制以队为基础,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土地由集体耕种,从事农活的叫社员,也叫劳力。我父母自然是社员中的一分子。每天清晨,他们与其他社员一样,踩着生产队长急促的哨声,到社场集中,领了任务,下地干活。按工分标准,男性壮劳力“足工”10分,其余的9分、8分;女性壮劳力“足工”8分,其余的7分、6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相应减少分值,也就6分、5分;未成年人3分、2分。这样的分值是评出来的,相对公平,但视情也会有所照顾,往往由生产队长说了算。工分算少了,个别“犟蛮”的社员找生产队长理论,即便争个脸红耳赤,生产队长也很少妥协。挑担、锄地、开沟、插秧、轧稻属重活,分值自然高些,大家心里有数。同时插秧,几个小后生谁快、谁慢、谁质量好,一目了然。谁记10分,谁记8分,清清楚楚。亮分时,队长一提议,基本通过。每月有合计,年终有累计,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娄葑公社群力大队社员围垦黄天荡,摄于1966年(图片来自苏州市档案馆馆藏)
当年,父亲还年轻,从不偷懒耍滑,舍得卖力气,累活脏活抢着干,每天都是“足工”,记10分。连年获评先进,领个奖状,10多年下来,墙上花花绿绿一大片。母亲年轻时是工人,在城里的工厂上班,但后来下放到她姑妈家所在的农村,嫁给我父亲后成了农民。前两年,因干农活不太熟练,算不了“足工”,出勤一天记7分。

1972年上半年社员劳动工分和肥料工分(图片来自网络)
为多挣点工分,未成年的姐姐和我,每到大忙季节,也会去凑数。大都干些除草、摘棉花等的轻活,当然插秧也干过。当时在我看来,插秧是天底下最累的活,还要遭长辈们奚落——“干活不像样”。插秧还得提防蚂蟥的叮咬,一旦咬上,撕都撕不开,常常鲜血淋淋。除插秧外,积肥也是苦差事。当年,肥料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农闲时节,生产队长给每户下达积肥任务,每一百斤草料记4分。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两天内,田埂、岸坡上便不见一根杂草。小小年纪的我只能站在齐胸的河水中捞水草,其中的苦难,现在的孩子是极难想象的。

插秧(图片来自网络)
即便是父母全年无休,姐姐和我多少也能挣点工分,到年底“分红”,相对于劳力多的家庭,我家几乎年年“透支”,印象中最好的年景,我家分了20多元人民币,只见父亲躲在房门后,粘上口水,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

沛县60年代工分票(半分) (图片来自网络)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乡队企业兴起,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我母亲落实了政策,每年领取生活补贴。姐姐进城当了工人,我考上了大学,弟弟做了裁缝,一家人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新世纪初,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在经历了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嬗变后,实现了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农活由职业农民干,机械化作业,原本的“农民”再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旱涝保收。现如今,生产队家家住楼房,户户有汽车,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小康生活。这一切,用辛苦了大半生、月月领养老金的父母的话说:“这样的好日子,以前连做梦都梦不到。”
两张社员证,一首变奏曲。
注:因作者外出,无法提供图片。文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原载于2018年7月28日的《苏州日报》B01版